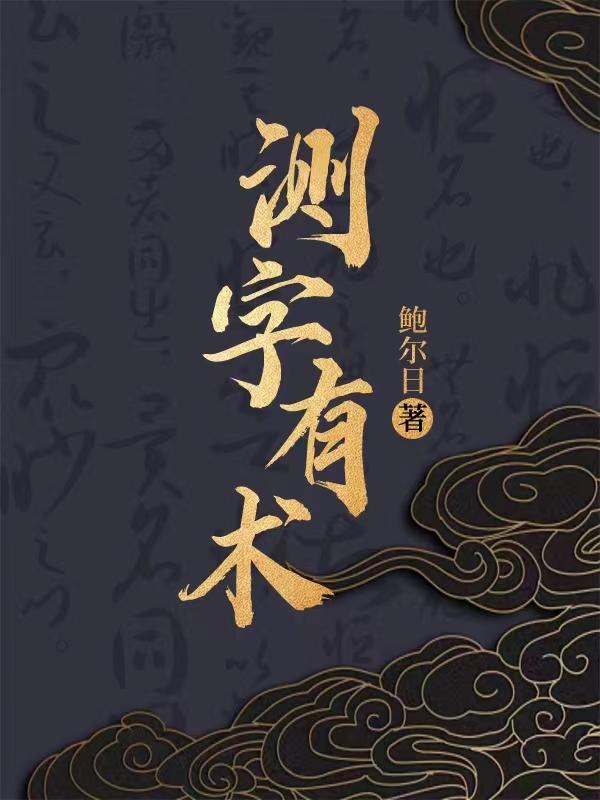笔趣阁 > 霓虹夜骨瓷白 > 第226章 幽途险嶂寻秘钥(第1页)
第226章 幽途险嶂寻秘钥(第1页)
幽窑启处邪氛荡,古道行来迷雾长。
此去险途寻秘钥,前尘旧梦系存亡。
*************************************************************************************************************************************
那股从窑口吹出的阴风,仿佛带着无数细小的冰针,刺入沈青临和阮白釉的肌肤,激起一片鸡皮疙瘩。窑内漆黑一片,深不见底,唯有那股混合了骨灰与怨念的独特气味,如同无形的向导,引诱着他们踏入未知的深渊。
沈青临深吸一口气,空气冰冷而滞涩,带着浓重的尘埃与一种难以名状的腥甜。他将手中那根已经弯曲变形的金属短棍握得更紧,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侧头看了一眼阮白釉,她的脸色在幽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坚定,那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然。
“我先进。”沈青临声音低沉,不带一丝犹豫。他清楚,这种未知环境下的第一步,往往伴随着最大的风险。
阮白釉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身体微微向后,让出通路,同时全神贯注地戒备着四周,尤其是他们刚刚脱离的那个布满裂痕陶板的区域,生怕再生变故。
沈青临猫着腰,率先钻进了那半圆形的窑门。一进入窑内,光线骤然消失,唯有从入口处透进的一丝微弱余光,勉强勾勒出窑壁粗糙的轮廓。脚下并非平坦的地面,而是布满了碎石和不知名的硬块,踩上去发出“咯吱”的声响,在这死寂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刺耳。
“小心脚下。”沈青临提醒道,声音在狭窄的空间里显得有些发闷。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巧但亮度极高的LED手电——这是他作为古董鉴定师勘探古墓或旧宅时常备的工具,此刻却成了他们在这绝境中唯一的光源。
光柱亮起,驱散了部分黑暗,照亮了眼前的景象。这是一条狭窄的甬道,勉强能容一人通过,窑壁由同样的青黑色砖石砌成,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烟熏火燎的痕迹,以及凝固的、颜色暗沉的奇异流淌物,仿佛是某种油脂或树脂在高温下融化后又冷却的产物。空气中那股混合气味更加浓郁,几乎令人作呕。
阮白釉紧随其后,一进入窑内,便感觉到一股比之前幻境中更为强大、更为原始的压迫感。这股压迫感并非来自物理层面,而是直接作用于精神,让她血脉中那股苏醒的力量再次躁动起来,仿佛遇到了同源而又相斥的存在。她下意识地握紧了胸前那枚贴身佩戴的、冰凉的玉坠,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她带来一丝慰藉与冷静。
“这窑……不像是烧普通瓷器的。”沈青临一边用手电四下照射,一边低声说道。光线下,可以看到窑壁上除了烟熏痕迹,还刻画着一些模糊不清的符号,与炉门上的符文风格相似,但更为潦草和原始,充满了疯狂与扭曲的意味。
“嗯,”阮白釉应道,她的目光锐利如刀,仔细分辨着那些符号,“这些符号……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类似的图案,一些非常古老的、关于祭祀仪式的孤本残页上……但这里的更加邪异。”
两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向窑内深处探索。甬道蜿蜒曲折,时而宽敞,时而狭窄,仿佛巨兽的食道。脚下的碎石越来越多,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破碎的陶片,颜色漆黑,质地与之前那块核心陶板类似,但更为粗糙,上面布满了细小的孔洞,似乎是某种失败的试验品。
沈青临用金属短棍拨开一块较大的陶片,发现下面压着一截焦黑的、类似骨骼的东西,但形状怪异,不似人类也不像任何已知的动物。他眉头紧锁,没有让阮白釉细看,只是默默记在心里。
越往里走,空气越发混浊,那股混合了骨灰、怨念、焦臭以及若有若无血腥味的气息,几乎凝成了实质。阮白釉甚至能感觉到,那些附着在窑壁上的暗沉流淌物,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似乎微微蠕动了一下,但再仔细看时,又恢复了死寂。
“青临,你看那里!”阮白釉突然指着前方甬道拐角处的一片窑壁。
沈青临将手电光束投过去,只见那片窑壁相对平整,上面用暗红色的颜料,描绘着一幅巨大的壁画。壁画的线条粗犷而诡异,内容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画中似乎描绘着一个盛大的祭祀场景,无数扭曲的人形跪伏在地,向着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窑炉顶礼膜拜。而窑炉之中,隐约可见两个纠缠在一起的、散发着不祥光芒的轮廓,仿佛是某种“双生”的存在正在被献祭或锻造。
“双生窑变……”阮白釉再次喃喃出声,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这壁画,无疑印证了她之前的猜想。这座古窑,绝非凡品,它本身就是一场巨大而邪恶仪式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