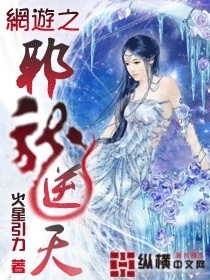笔趣阁 > 妄折春枝 > 第199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第2页)
第199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第2页)
永宁侯回想起房中那不堪入目的一幕,心头猛地一颤,慌忙后退数步,唯恐沾染上半分污秽。
真是让人心有余悸啊!
常人唯恐鲜血沾身,到了他这儿,倒成了惧怕屎尿溅衣。
裴临慕僵住了。
赤裸裸的嫌弃,根本不加掩饰。
但,他不敢表露出丝毫的不忿,忙请罪道:“儿子失态,请父亲宽恕孩儿的无心之过。”
“实在是那躲在暗处害人的贼人其心可诛!”
裴临允急的跳脚:“怎么就其心可诛了!”
他用的不过是些大黄、巴豆之类的泻药,又不是什么砒霜、鹤顶红这等见血封喉的剧毒!
永宁侯和裴临慕异口同声:“所以,真的是你?”
裴临允呼吸骤然一滞,眼神飘忽不定,略显局促地偏过头去,声音细若蚊呐:“我不过是在酒坛里撒了一小把泻药……那日他设计害我在先,我不过是想让二哥当众出丑罢了。”
“这世道,难道只许他暗算我,就不许我回敬一二?”
话音未落,又急急补充:“可我终究念着血脉亲情,断不会要了二哥性命。”
“父亲明鉴!二哥之死与我绝无干系。古往今来,谁听说过巴豆大黄能顷刻间要人性命的?”
越说,底气越足,索性回正脸,挺直腰板,猛地指向裴临慕,声音陡然拔高:“三哥今夜也饮了那加料的酒,如今不也好端端站在这里?不过就是多跑了几趟茅厕而已。”
最后这句说得掷地有声,仿佛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父亲明鉴,定有其他人在背后兴风作浪。”
这下,轮到裴临慕错愕了。
裴谨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