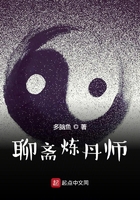笔趣阁 > 快穿之气运男主的黑月光 > 第221章 女配是真恶毒20(第1页)
第221章 女配是真恶毒20(第1页)
暮色像打翻的墨汁,渐渐浸透了整个村庄。苏宇踩着露水来到孙家小院时,月亮刚爬上老榆树的枝头。
孙寡妇正在晾晒草药,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听到脚步声,她头也不回:"药在石桌上,三碗水煎成一碗,早晚各......"
"庆姐。"
这声呼唤让孙庆的手顿在半空。她转身时,鬓边的碎发被夜风轻轻拂动,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上还沾着草药渣子。
"给婶子摘的。"她把粗布包裹的药包往前递了递,眼睛却盯着地上两人的影子,"川断和骨碎补,要文火......"
苏宇突然抓住她的手腕。
年轻小伙子的掌心滚烫,烫得孙寡妇心头一跳。
她这才发现,当年跟在她身后捡麦穗的毛头小子,如今手指关节已经粗粝得硌人。
"明天就要定亲了。"孙庆猛地抽回手,声音比晒干的草药还脆生,"你这是干啥?"
月光下苏宇的喉结滚动了几下:"我......你知道的,我不想的。"他攥着药包的手指节发白,"家里催得紧,你只要愿意,我......"
"我不愿意。"孙庆打断得又快又急,像在害怕自己会后悔,"我只把你当弟弟看。"
这句话像把钝刀子,在两人之间划拉出一道看不见的血痕。
孙庆低头整理晒药的竹匾,指甲缝里还嵌着采药时沾的泥。她闻得到苏宇身上新衣裳的棉布味——那是为明天定亲特意置办的。
"以后别说这些话了。"她转身往屋里走,背影单薄得像张剪纸,"代我问婶子安。"
苏宇伸出的手悬在半空,最终只抓住一缕带着药香的风。
月光把他的影子钉在原地,而孙庆的窗户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
灯影里,她正把什么东西塞进炕头的木匣子——那里面装着三年前苏宇送她的,一支已经干透的野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