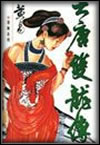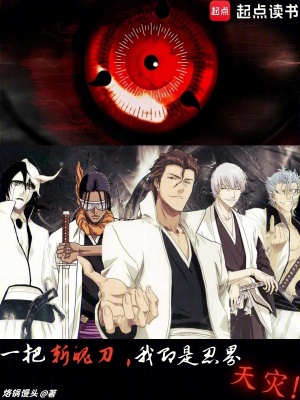笔趣阁 > 姐夫帮你打天下 > 第1054章 邓庄年会(第2页)
第1054章 邓庄年会(第2页)
孔柳摇头。
"元帝时,有个叫贡禹的儒生上书,说应该恢复井田制。"邓晨冷笑,"可当时全国七成土地已在豪强手中!这些满口仁义的儒生…”邓晨突然攥紧拳头问道:”谁真正去田间看过饥民?"
邓晨在现代读史时,曾看过西汉末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短短二十年锐减四成。
孔柳的手指无意识地卷着衣带:"所以你认为..."
"不是我认为,是历史证明。"邓晨回书房取出一卷竹简,"这是常山郡的田册。推行'限田令'后,流民返乡者增加了三倍。"他忽然苦笑,"可朝中诸公还在争论该用《周礼》还是《王制》..."
晨风吹动孔柳的鬓发,露出她紧锁的眉头。邓晨的话像把钝刀,正在一点点剖开她坚守多年的信念。
"我父亲..."她声音发涩,"他其实...一直想改革官学..."
邓晨眼睛一亮:"那就从常山开始!"他激动地抓住孔柳的手,"我们办新式学堂,既教圣贤书,也教..."
"算术格物?"孔柳突然接话,嘴角微微上扬。
两人相视一笑,昨夜的剑拔弩张仿佛从未发生。院角的梅树上,一只麻雀扑棱棱飞起,抖落无数晶莹的露珠。
次日一早,他叫来了邓沙,听取邓庄最近的发展情况,总体向好,外面的战乱虽然多少还是影响了邓庄,但是并不大,反倒是因为战乱,不断接收一些流民,邓庄变得更大了。而且以老带新,进入良性循环。
邓晨坐在议事厅的主座上,手里捏着一份名单,眉头微皱。
邓沙站在一旁,搓着手,脸上堆着笑:“少主,您看,今年咱们邓庄又壮大了不少,光是新收的流民就有八百多人,现在庄子里能干活儿的青壮年都快两千了。”
邓晨点点头,手指在名单上轻轻敲打:“嗯,不错,不过……”他抬头看向邓沙,“我怎么觉得这名单上的人名,有一半我都不认识?”
邓沙干笑两声:“这不是您一直在河北嘛,庄子里新提拔了不少骨干,都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