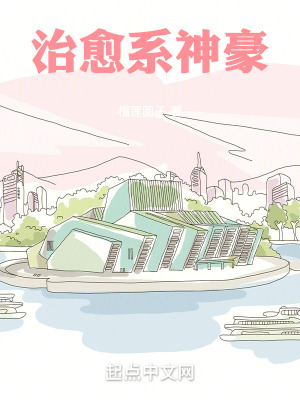笔趣阁 > 穿越七零年代当绣娘 > 第415章(第1页)
第415章(第1页)
老者镜片后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片刻,似乎在确认什么,随即点了点头,嘴角牵起一个极淡、极有分寸的笑意,口音带着清晰的、柔软的南方腔调:“是颜简韵同志吧?鄙姓沈,沈伯安。打扰了。”
“老人家,您好。”颜简韵应着,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插进锁孔。
铜锁“咔哒”一声弹开,她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侧身让了让,
“您请进来说话?” 沈伯安微微颔首,步履沉稳地走进小小的院落。
院子不大,收拾得干净利落,墙角几盆常见的月季开得正盛,砖地上连片落叶也无。
颜简韵把自行车靠在墙根,引着客人走进正屋。 屋内陈设简单,桌椅擦得发亮。
最显眼的,是靠窗那张宽大的旧榆木桌子。
此刻,桌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铺着一块深蓝色的厚实绒布。
绒布上,端端正正摆着一个半米见方的绣绷。
绷子绷得极紧,绷面上,是一幅已完成了大半的牡丹图。
丝线在斜照进来的夕阳余晖里流淌着柔润的光泽,花瓣层层叠叠,仿佛带着露水,饱满得下一秒就要从绷子上滚落下来。
旁边的针线箩里,各色丝线分门别类,缠绕在光滑的竹绷子上,细如牛毛的绣针整齐地别在一块深色绒布上,闪烁着细碎的银光。
沈伯安的目光瞬间被那绷子牢牢吸住,他下意识地向前一步,微微俯身,镜片几乎要贴到那绚丽的牡丹花瓣上。
他看得极专注,手指在身侧无意识地捻动了一下,仿佛在隔空感受那丝线的韧度与针脚的走向。
颜简韵无声地放下自己的帆布挎包,没有急着招呼,只是安静地站着,目光落在老者专注的侧影上。
空气里只剩下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归巢麻雀的啁啾,和老者细微悠长的呼吸声。
夕阳的金辉穿过窗棂,将他花白的鬓角和专注凝视绷面的神情镀上一层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