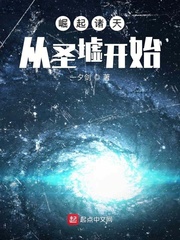笔趣阁 > 幸福家庭(母子哨向 1v2) > 063只敢抚你发端(第3页)
063只敢抚你发端(第3页)
他沉默了很久。
最终,他从领口里抽出一根吊绳,在吊绳的底端,钻孔而过,挂着一颗发黄的乳牙,牙齿的结面被摩挲到光滑莹润。
她的叹息长如暗夜。
18岁的莱斯利曾有个从未索要出口的答案。在他们结伴前往学院的前一天,el将手里抱着的纸袋递给她,纸袋里装满为出行准备的物什:她贴身的衣物,el用于剃胡子的组装刀片,二手的铜扣皮带,两份简陋的路餐——两片薄且透明的杂粮面包中夹一片干瘪的火腿。
她望着el后退一步,单膝跪下。
有那么一个瞬间,她以为他会求婚。
她等了一会。
尘埃在午后阳光中落下的速度无限延缓,他膝盖撞在沥青地面,分秒在这琐碎的日常细节中迟滞爬行。
他犹豫片刻,低头,系紧了松脱的鞋带。
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快步走开,像逃离一场尚未上演的独角剧目。
“那时候,是我自作多情吗?”
“不是。”他坚定地说,“从来不是。”
他们肆无忌惮、毫无回避地谈论过去。
因为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不会有任何联系。
el在她耳边悄悄耳语,轻口咬着细密的碎话。直到有人不耐烦,l朝外挪开她的膝盖,他们不再互相盯着对方的膝盖。她比他勇敢,勇于直视一切。
她直视他的眼睛,“你知道我要来做什么的。”
他微乎其微地叹一口气,下颌轻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