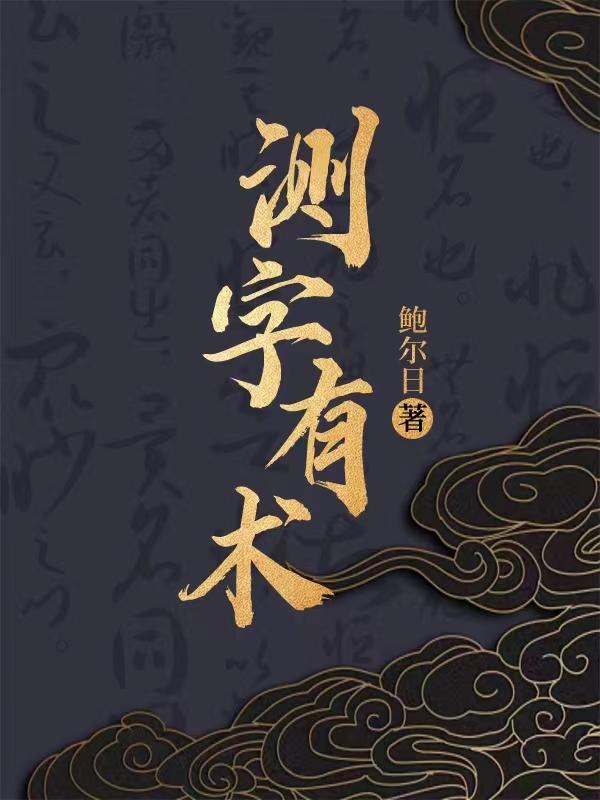笔趣阁 > 大明第一相 > 第148章 橘枳(第1页)
第148章 橘枳(第1页)
楼上有一竹篮,篮中别无他物,只有一个陈旧的酒坛子,也没菜,倒是有几个青橘。
夏汉升将砚台用丝绢包好放入篮中,又起身笑道,“我们是堂兄弟,我是长房,他是三房,我年长几岁,他要唤我一声二兄。”
见李步蟾有些异色,夏汉升问道,“步蟾老弟此次来府城院试,廪保办得如何了?”
李步蟾摇头苦笑,夏汉升一拍大腿,咧嘴笑道,“前几日我就听朋友说起,那卢景玉跟人传过话,不让给你廪保,看来此言还真是不虚。”
“那日他们落了颜面,也难怪……”
李步蟾的话头被夏汉升截断,他一拍栏杆,“什么难怪,技不如人,不思三省自身,只会鸡鸣狗盗,算什么圣人子弟?”
李步蟾嘿然一笑,圣人子弟的标准如何,一千个圣人子弟,有一万个哈姆雷特。
“不就是廪保吗,愚兄也是府学廪生,这事你就别管了,包在愚兄身上。”
夏汉升拍拍胸脯,大大咧咧地道,“明日有事,后日巳时,我们去府衙礼房,将院试的结票办了,如何?”
能得到夏汉升的襄助,李步蟾挺高兴,这算是意外之喜,省了不少事儿,但他又有一些迟疑,“那感情好,不过……”
“老弟放心,我与老六素来不睦,他那人太他娘的……你知道这块砚是个什么来历么?”
夏汉升撇撇嘴,对夏文升的吐槽到了嘴边,又吞了下去,李步蟾毕竟是外人,有些东西在家里说说还行,外扬却是不妥。
“这方砚台,是老祖少年所置,当时失祜家贫,只靠老安人独力维持,读书大不易,却仍花钱买了这方端砚,这方砚现在看来简朴粗砺,但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这方砚台,一直陪着老祖参加科试,入国子监,到户部任职,二十年不弃,都已经磨得凹了。”
夏汉升负着双手,追慕着先祖,“建文年间,老祖任户部侍郎,南下采访,途中归乡,曾在橘洲小住,这方砚台却被侍婢给弄丢了,侍婢既怕又愧,一急之下,便欲投缳自尽,老祖闻知之后,让她不要放在心上,宽慰她道,世间万物有枯有荣,有得有失,怎么能重器物而轻人命呢?”
夏汉升这人有些话唠体质,说起他崇拜的曾祖来,便没完没了。
“老祖宽厚,当年巡视苏州,谢绝了知府宴请,就在客栈进食,不想厨子做菜太咸,无法入口,他怕厨子受责,便说自己胃口不好,只吃了些白饭充饥。
后来老祖巡视淮阴,马儿一个没看好,跑了没个踪影,跟路人询问,不想那路人脾气火爆,他正着急赶路,非但没有回答,还怒骂老祖像条笨牛,刚好地方官赶到,吓得肝胆俱裂,要抓住那人问罪,却被家祖所止,说是本来就是自己耽误了人家赶路,怎么能因为自己之过反而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