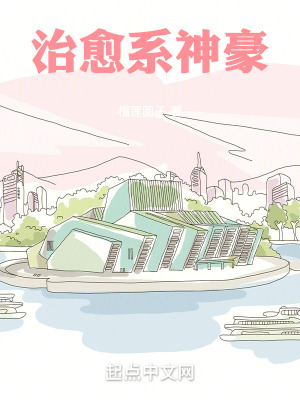笔趣阁 > 不是替身吗?她怎么捧权臣称帝了 > 第59章 夜探承禧宫(第1页)
第59章 夜探承禧宫(第1页)
子夜三刻的冷风卷着雪粒子,扑在萧煜玄狐裘的毛边上。
他踩着承禧宫结霜的青石板,靴底碾碎了几片枯荷——这原是苏映瑶前世最爱的景致,她总说“残荷听雪比盛荷更有风骨”。
李公公提着宫灯的手直抖,灯穗扫过朱漆门柱时蹭下块漆皮:“陛下,陈嬷嬷晌午才来收过炭盆,说娘娘搬去墨府半月,这殿里的帷帐都收进樟木箱了。”
萧煜没应。
他望着空荡荡的妆台,青铜镜蒙着层薄灰,镜沿还卡着半枚褪色的绢花——是苏映瑶前世亲手做的,那年他去御花园赏梅,她追出来要替他别在衣襟上,他嫌花色素淡,随手搁在了妆台。
“啪嗒。”
他的指尖抚过金凤衔珠簪的插槽,那是苏映瑶入宫时苏家送来的陪嫁,前世她总说“皇上嫌我素净,我便戴得热闹些”。
可他从未留意过,这簪子的金叶纹路与苏家祖宅影壁上的云纹竟如出一辙。
“陛下可要瞧瞧暗格?”陈嬷嬷的声音从廊下传来。
这位在承禧宫当差二十年的老嬷嬷,此刻裹着灰布棉袍,鬓角的白发被风吹得乱蓬蓬,“娘娘走时说,若有人来寻,便提提她抄的偏方。”
萧煜的手顿在妆台右侧的雕花处——他记得这暗格,前世苏映瑶总说里面收着《女诫》批注,他嫌她迂腐,从未看过。
此刻暗格被陈嬷嬷推开,露出半本泛黄的《药典》,残页边缘还留着墨渍,正是他昨夜在御书房攥碎的那半页。
“这方子治的是先皇后的旧疾。”陈嬷嬷走近两步,袖口沾着承禧宫特有的沉水香,“娘娘说,当年先皇后咳血,太医院开的方子总差一味引子。她在佛堂抄经时听老尼提过,便日日去御药房翻典籍……”
萧煜的指尖在残页上发颤。
前世他总觉得苏映瑶抄经是作秀,却不知她抄的不是《女诫》,是《千金方》;他嫌她总往御药房跑是攀附太医院,却不知她是在替先皇后找救命的方子。
“娘娘还说,这《药典》抄完该呈给陛下的。”陈嬷嬷的声音突然哽住,“可那年陛下说她‘心思深沉’,将她的药罐摔在承禧宫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