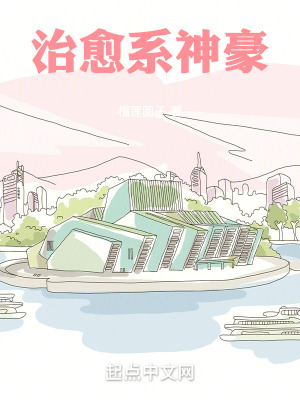笔趣阁 > 不是替身吗?她怎么捧权臣称帝了 > 第59章 夜探承禧宫(第2页)
第59章 夜探承禧宫(第2页)
廊外忽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赵侍卫的玄色披风撞开垂花门,他腰间的佩刀擦着门框发出锐响:“启禀摄政王,又逮着个穿司礼监服饰的。”
声音飘得很远,却清晰撞进萧煜耳中。
他踉跄着扶妆台,鼻尖突然涌上来世熟悉的沉水香——前世苏映瑶总爱在承禧宫点这种香,他嫌味道淡,命人换了龙涎香;今生她搬去墨府,倒连这香都成了承禧宫最后的余韵。
“王爷该去更衣了。”
另一道声音从宫墙外传进来,是苏映瑶的。
萧煜猛地抬头,承禧宫的飞檐外漏出点灯火,像是墨府东院的方向。
他想起昨夜御书房外,她披着墨羽寒的大氅,鬓边银蝶簪缺了半片,却比前世戴满翡翠时更亮。
“夫人今日批的河工文书,比本王早了三个时辰。”墨羽寒的笑声混着风声传来,“漕运司那笔贪墨,连本王都差点漏了。”
萧煜攥紧《药典》残页,指节泛白。
他忽然想起素绢上那幅画——苏映瑶站在河工司碑前,银蝶簪的断口闪着光。
前世她总说“妾不懂朝政”,原来不是不懂,是他从未给过她懂的机会。
“陛下。”李公公的宫灯晃了晃,将两人的影子投在褪色的《河图》上,“该回御书房了,明日早朝还要……”
“闭嘴。”萧煜打断他。
他望着妆台暗格里的《药典》,忽然想起前世苏映瑶咽气前,手里攥着半片银蝶簪。
那时他在柔仪殿陪表妹赏雪,是李公公来报的信,说贤妃“去得很安静,手里还攥着块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