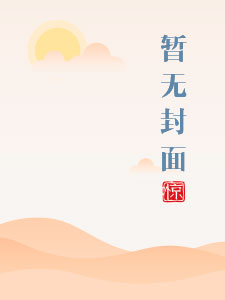笔趣阁 > 修行王朝 > 第76章 自取灭亡(第3页)
第76章 自取灭亡(第3页)
乾隆五十七年,当时的礼部尚书建议会试考校《春秋》,并且不使用胡安国注解的《春秋》,因为胡安国注解的春秋能够拿来作为考点的也就十几处,很多考生并未完全读完《春秋》,而是记住了那些考点。
但就算如此,治《春秋》的人还是太少了。
因此,在读书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将《春秋》和《礼记》作为本经的人,要么是狠人,要么就是傻。而这些治《春秋》和《礼记》的书生,也会看不起其他三经,特别是《诗经》。
其实科举的重点还是在四书,甚至在科举的比重中,四书的比重也会比五经要高,就算你五经没有答好,但是在答四书题时写的好,也能高中。
乾隆皇帝,也就是我们的章总曾说,“科举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
所以从五经延伸出来的,就是读书人之间的一条鄙视链了。于是在听到周俊说自己的本经是《诗经》之时,何正才会露出一丝鄙夷。
“原来是《春秋》,看来何巡检治经水平不行,虽然将《春秋》作为本经,但是却看不懂,所以才屡次落第。”
周俊的这话不仅是说何正治学水平不行,而且还嘲讽何正没有考中进士,只是一个举人。
何正毕竟不是周俊,没有他那么隐忍,或者说何正作为何家人,又是上虞的巡检,平日里都是别人顺着他,哪有人敢过来抚他的逆鳞。
当即便反唇相讥,“不知尊使有何功名在身?”
周俊当即有些恼怒,这其实算是他的一个痛。他仅通过了童生试,也就是取得了秀才功名,后来便加入了白莲教,从此再没有踏入过科考考场。
此时何正拿一个举人来激他,要是换了一般人,恐怕已经发作了,更何况周俊还是何正名义上的领导。
周俊深吸几口气,脸色平静道:“比不得巡检,某只是一个小小的秀才。”
何正此时不知道是有沉浸在赢了周俊的飘飘然里,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上虞县作威作福惯了,并未听出周俊这句话里蕴藏的怒意。
只听何正道:“原来只是一个秀才,与一秀才议论本经,实在是不妥,在这里向特使谢罪,是本官考虑不周了。”
这哪里是考虑不周啊,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啊。
但是周俊依然忍下来了,不得不说在白莲教中能从一个秀才到如今特使,周俊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别的不说,这个隐忍功夫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其实,换做平日里,或者说换一个人这么和他说话,那人坟头草估计都有几米高了,他之所以能忍下来,还是因为何家以及巡检这个位置对白莲教而言十分重要。
上虞县是南平府府衙所在,而这处巡检司驻地驻守在水陆交通要道,将这里称之为上虞县的门户也不遑多让,许多南平府发往荠县等县城的行政命令,都会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才有驿馆,巡检司衙门才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