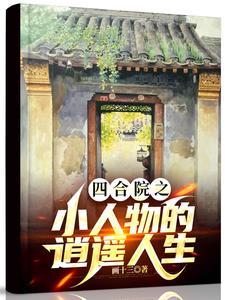笔趣阁 > 江花玉面 > 第514章 彼岸花(一)(第1页)
第514章 彼岸花(一)(第1页)
温北君的意识在虚空中浮沉,仿佛一片凋零的梅瓣在无尽长夜中辗转。刺骨的寒意浸透魂魄,记忆的碎片如冰棱般刺痛神魂。忽然,一缕幽香沁入灵台,眼前渐渐浮现出一条蜿蜒小径。路旁盛开着血色的彼岸花,花瓣上凝结着晶莹的露珠,每一滴都映照着往事的碎片——有碧水在梅下抚琴的侧影,有瑾潼踮脚为他系上平安结的小手,还有战场上漫天飞舞的旌旗与血雨。
花丛深处,玄甲青袍的将军负手而立。月光穿透他半透明的身躯,在地上投下淡淡的影子。那道横贯额角的剑痕仍在渗血,暗红的血珠顺着眉骨滑落,在彼岸花上溅开细小的红梅。
"温北君,这彼岸花可还认得?"李长吉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谑,指尖轻抚过颈间那道狰狞的伤口,"当年在淮水对峙时,岸边开的正是此花。你那一刀刺穿别人咽喉时,我的血把这花染得比现在还要红。"
温北君凝望着花瓣上滚动的血珠,忽然想起那个血色黄昏。无数的颈血喷溅在岸边的野花上,将原本洁白的花瓣染得猩红。如今才知,那竟是开在阴阳交界处的引魂花。
"李长吉..."温北君的声音沙哑,"当年淮水之战..."
"不必解释。"李长吉摆手打断,玄铁护腕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各为其主,生死相搏本是常理。倒是你..."他突然凑近,沾血的手指虚点温北君心口,"这些年可曾睡过一个安稳觉?"
温北君默然。无数个长夜里,那些死在他刀下的亡魂总会入梦索命。最常出现的,正是眼前这个被他赐死的文人。
小路尽头,漳水泛着幽蓝的磷光。水面漂浮着无数盏河灯,每盏灯芯都燃着青色的火焰。仔细看去,灯纸上竟写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都是曾经追随他战死的将士。
"你的亲兵统领赵七,特意为你扎了这些灯。"李长吉指向最近的一盏,灯焰突然窜高,映出"先锋营三百将士"几个小字,"他说黄泉路冷,要给你照个亮。那小子现在在阴司当差,专管引魂渡河。"
温北君伸手去触,指尖穿过冰冷的火焰。刹那间,三百张年轻的面孔在火光中浮现——有憨厚笑着的胖厨子,有总爱偷喝酒的瘦高个,还有那个脸上带疤的娃娃兵...转瞬又消散无踪。他忽然记起,当年在玉门关外,正是这些儿郎用血肉之躯为他挡下了吐蕃的箭雨。
"赵七他...还好吗?"温北君的声音有些发颤。
李长吉轻笑:"那小子现在可威风了,手下管着八百水鬼。就是总念叨着要给你当亲兵..."他突然压低声音,"其实这些灯里都藏着他们的执念,你要不要听听?"
不等回答,李长吉已拂袖轻挥。最近的那盏河灯突然剧烈摇晃,灯焰中传出整齐的呐喊:"将军!先锋营三百将士,请战!"
温北君浑身一震。这是当年临仙城外,三百死士冲向箭雨前最后的请命。他记得自己亲手为他们斟的壮行酒,记得那个娃娃兵临行前偷偷把家书塞给他,更记得三日后在乱尸堆里找到的、紧紧攥着"温"字军旗的断手...
李长吉取出一个鎏金酒壶,壶身刻着"醉卧沙场"四个篆字。斟酒时,酒液竟呈现出诡异的青蓝色,与河灯的火焰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