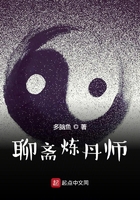笔趣阁 > 《酒与枪》作者:梦也梦也 > 第362章(第2页)
第362章(第2页)
那是个相当专注且认真的吻,当一个人剪断炸弹的最后一根红线、或者是外科医生小心地进行心脏手术的时候会露出那种神情。
阿玛莱特亲吻自己的伴侣的时候不像是面对一个人。而更像是小心翼翼地用嘴唇探索一个精密的机器表面。这机器的核心是有自己的思维的,而正如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诸多想象一样,没人知道它到底决定帮助人类还是毁灭人类。
在这个时刻,斯特莱德心里竟然还能流淌出这样狂乱而怪异的念头,更多不连贯的词语从他脑海中飞过,一些求救,疯狂的自嘲,绝望的哀嚎,还有不熄的一角怪异地想着上帝啊他确实是我偏爱的那个类型。
无论是多年之前还是现在都是一样。
他本身就是一个凝聚着恐惧和疯狂的旋涡,阿玛莱特也是如此。这栋教堂不只是教堂,是涌动着狂乱的暗流的黑色水域,那和年轻人在祭桌上被脱光衣服,像是一场燔祭,水面上惨白的浮尸,被开膛破肚的羔羊。
当阿玛莱特把那个年轻人操出一连串不流畅的呻吟的时候,斯特莱德的脑子都还是一团浆糊。
他双臂剧烈疼痛,深陷恐惧之中。而维斯特兰钢琴师显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跟别人做爱是个好主意
黏腻的水声,被架在臂膀上的微微颤动的小腿,一截绷在皮肤上的黑色的袜带(衬得皮肤格外洁白,黑得就好像是一种嘲讽),而斯特莱德只能感觉到心脏在剧烈的跳动,他甚至已经感觉不到多少诡异了。
他当然记得那个年轻人的脸,以他之前知道的所有信息而言,那个年轻人本应该死了,死在赫斯塔尔?阿玛莱特手下,是对方绝望爱情的一个悲惨的脚注……
但是实际上他显然没有。而且如果斯特莱德没弄错,看阿尔巴利诺?巴克斯把人流畅地挂在钢琴弦上的动作,那整整一船的死人很可能都是他弄到这来的。
于是真相在此刻如此明了:真相就写在巴克斯那个透出些疯狂神色的笑容里,在他那双游荡的萤火一样绿的眼睛里,在那些花朵之中。
斯特莱德意识到,他也正同时面对着礼拜日园丁。
这多么讽刺啊,他的不幸从赫斯塔尔?阿玛莱特开始,显然这个小时候足够安静的孩子长大后成了个连环杀手,还成功地和另外一个连环杀手搅在一起,这话说出去能叫任何一个人发疯。
一个连环杀手会选择另一个连环杀手,死亡也好,爱情也罢,都是他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疯狂戏剧,在所有人都为阿玛莱特这样一个人的悲惨爱情而奉上自己的掌声的时刻,黑暗里有从未登台的演员抽出藏在身后的尖刀。
斯特莱德的嘴里含着一堆惊恐的咒骂。疯子。魔鬼。但是他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此刻目眦尽裂,但是似乎他连目光都没法从那交缠的人体上移开。
他看着那疯子的手在洁白的桌布上收紧了,斯特莱德看见自己的血从手臂上的伤口中淌出来,沿着那些挂在天花板下的钢琴弦流淌,浓郁地覆盖住了琴弦本身的金属质感,在不堪重负之后终于坠落下来,发出啪的一声,一滴一滴地落在洁白的桌布上,像是走向那个躺在祭桌上的金发年轻人的一串脚印。
他看见那些布料之间的褶皱如同微缩的山川。而他想到了白橡镇,想到了教堂,想到了那些浸透在罪恶的夜色里的玻璃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