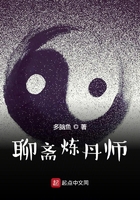笔趣阁 > 《酒与枪》作者:梦也梦也 > 第390章(第3页)
第390章(第3页)
不知道有多少躺在医院里等死的患者曾与他配型成功,但是所有人都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最后,他的哥哥很忧郁地叹了一口气。
“唉,”他低声说道,“可惜最后没能捐献成功。”
在教堂的葬礼结束之后,仪仗队护送着棺椁前往墓地,墓穴已经挖开,湿润的泥土如同暴露的伤口,袒露在阴恻恻的铅灰色天空之下。
黑色的汽车车队在街道上蜿蜒前行,数千送葬的人们尾随其后。参加葬礼的警官们身着全套制服,六名护柩者将覆盖着国旗的黑色棺椁抬向墓穴,棺椁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肩上,乐队演奏起风笛。
虽然亨特对追查罪犯确实兴致勃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反社会者。
实际上,他一直都很不喜欢葬礼这种过于悲伤的情景,这让他的心口发紧
在他干这一行之后,已经见过太多死人了,他一直希望以后不要再出席那么多葬礼,但是看来事与愿违。
尽管他一向不太喜欢麦卡德。但是葬礼的悲伤氛围依然让他感觉到太过压抑,他不想在奥尔加面前失态,就稍微离开了人群,在离致哀的人们较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等到自己稍微缓过一口气来再回去。
他回去的时候,看见奥尔加正在和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说话不过参加葬礼的人太多,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他恐怕都没见过。那是个相貌还算英俊的黑发男人,蓝色的眼睛在阴沉的天空之下稍微有些发紫(就好像伊丽莎白?泰勒一样,当时亨特不合时宜地想道)。等到亨特走近了一点之后,就能清楚地听清他们说话的内容。
“我看了一些报道,”那个男人说,他的英语发音有一股很微妙的伦敦腔,“很多人都指出,你和麦卡德探员的关系并不太好。”
那不会是个记者吧?亨特提高了警惕,时刻做好把对方赶出葬礼的准备。
“可以那样说,”奥尔加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对某些原则性的事情的看法有些分歧他在犯罪心理学上颇有造诣,也能够很明白地看穿人心,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做出选择我并不认同。”
“选择?”那男人问道。
“认为人们依然值得他拯救的选择……用他自己的方式。”奥尔加轻轻地哼了一声,平静地环顾四周悲伤的人群,“而无论从任何角度上来说,这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人不能改变时代的狂潮的流向,更况且他又不打算做希特勒;于是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只能以失败告终,我相信他自己也是明白的。”
那个男人顿了顿,露出一个仿佛是沉思的表情,然后他问:“那么现在呢?”